克劳利:现代世界的先知

阿列斯特·克劳利
0.导读
我打算将Bogdan教授的这一篇关于黑魔法师克劳利的长文分章节译出,以作为日后关于20世纪神秘学理论讲座的教材。读者若是细读本文,且对比之前叶芝研究的两期文章,就会发现研究神秘学的学者和文学学者之间,对待神秘学思想是极其不同的。
由于注解写得太多,在这里就不多废话了。关于标题的“现代世界的先知”,还有许多玄秘的解释,我不打算在翻译的文章中添加太过深奥的东西,以后的讲座可能会有,也可能不会。
我去年参加杜奎特大师(Lon Milo DuQuette)的课程,他继承了克劳利的许多东西。但可以想象,对“透特塔罗”感兴趣的人非常多,但愿意深入研究克劳利体系的人是凤毛麟角(当然一个人有资质和他愿意努力,是两回事)。这就是既往一切人类时代有关神秘学和灵性议题的一般写照,我只能说,大家开心就好。
作者简介:
亨里克·博格丹(Henrik Bogdan)是瑞典哥德堡大学宗教研究的教授,是欧洲西方神秘学研究协会(ESSWE)秘书。他主要研究的领域为:秘密协会、新宗教运动(NRM)以及西方神秘学。其出版的著作有《灵性启蒙仪式和西方神秘学》(2007)。
1.克劳利其人
阿列斯特·克劳利(1875-1947)这个人,在西方的主流文化中,被定义为如下身份:首先,他是一个离经叛道、极其邪恶的人物;其次,他被视作是当代各种撒旦思想(Satanism)的教父;在克劳利死后,尤其在一些流行歌手和摇滚乐手的塑造下,他还被视作各种过激行为(从性到Drugs)的鼓吹者。那么像克劳利这种嬉皮人生,不是更适合地摊文学和故事会么?为什么会吸引当代学术研究的关注呢?
针对克劳利的学术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留下的遗产和影响一直在不断被重新评估和认识。在20世纪,克劳利是一个相当具有影响力的、综合了各种宗教观念的人物。他的神秘学思想,并不是对中世纪世界观的回归;恰恰相反,在自身不断求索的过程中,克劳利显示出了现代性的先兆。他承认,自身败坏的名声变成了一层有效的滤网,以筛除那些无知轻信之辈,同时也全然阻挡了同行们对他的形而上学体系的接受。他仅仅是站在一旁,称自己乃是天煞孤星:其使命是作为一位洋溢着个人魅力的先知,站在人类新世代(dispensation)(注:这个词语在现代神秘学中极其重要,它的含义涉及到与宗教相关的大周期。这种周期观不同于神智学对印度传统中周期的阐释【神智学专题03】不朽圣域(上)布拉瓦茨基夫人论终北之地 【传统主义专题02】不朽圣域(下)盖农论终北之地 ;在叶芝【黄金黎明专题03】诗学与魔法 的作品《幻象》/A Vision中,他详细地描述了这种双螺旋结构的周期变化:叶芝的周期轮转理论以2150年为循环,以两种螺旋交替呈现,第一种被称为Solar/太阳的或Primary/主要;第二种是Lunar/月亮的或Antithetical/对立的。前者乃是“使人类与不可见世界相连接”,而后者则意味着“人造的文明与世俗化生活”。交替的意思是:类似于阴阳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个周期的上升意味着另一个周期的下降,二者会在运动的顶点形成最大张力——一方扩张到最大值,另一方缩小到最小值,此乃极度动荡之征兆。以近期历史来看,公元前44年凯撒被刺与80年后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两件事情,标志着上一个月亮周期扩展到最大,而这一个太阳周期开始发端。在公元5世纪前,世俗权力仍然是强盛期,但一直在走下坡路;与之相对的,基督宗教尽管备受压制,但一直在不断发展。这种发展直到公元1050年左右达到顶峰,再开始衰落。一千年后的20世纪,再一次出现类似两千年前、但相反的情况——世俗化的循环扩张到最大,宗教的循环坍缩到最小。因此,叶芝在其诗歌《二度降临》中有这样的描述:Turning and turning in the widening gyre/The falcon cannot hear the falconer/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re cannot hold/Mere anarchy is loosed upon the world。在这篇文章中,克劳利对新世代的理解也是在这个层面上展开的)的大门前,向每一个人宣告:以前诸多世代的道德准则和宗法规约都行将入土,失去效力,不必再理会,而每一个个体则拥有自我实现的绝对自由。个体若想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借助神秘学的工具——也就是克劳利所谓的“魔法”(Magick)。(注:就这一点而言,magic更多地指“舞台魔术”即Stage Magic,而magick则指真正的魔法)克劳利观念中的“魔法”具有高度的折衷性和个人化,其融合了诸多灵性实践,例如欧洲的魔法传统,以及来源于印度传统的冥想和瑜伽训练。在实现自性解放的道路上,克劳利还加入了性力,使其作为一种魔法训练。克劳利认为性魔法是实现法师们圣化目的的一种简单、有效且直接的方式,并不需要仪式魔法那么多花里胡哨的物品。因为,性魔法所蕴含的力量本来就深藏在实践者的心智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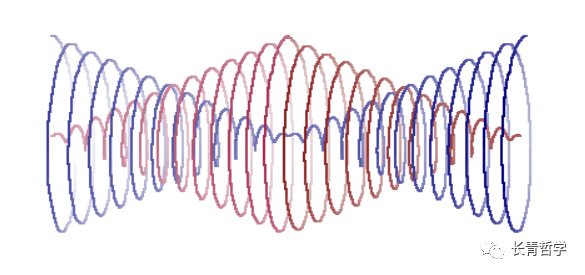
叶芝的双螺旋结构:钻石与沙漏(The Diamond and The Hourglass)
2.“科学之方法,宗教之目的”
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宗教运动的推动者,克劳利并不完全符合“神启者”这一笼统的概念。相反,他是在似乎没有放弃原有世界观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注: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以前的先知,例如《旧约》中的摩西、以利亚、但以理等,都是在短时间内接受“神启”而成为先知的。但克劳利显然不属于这种路径)在他给自己立“新时代的先知”的人设,以及作为《律法之书》(1904)文本的发布者(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就像“一封信的风格一样无法改变”)之前,在大学时代,他努力地学习哲学和经验科学。他那时极力反对童年时代所接受的、《圣经》准确无误的原教旨信仰,因此,在剑桥的时候,他开始去寻找,能够在业已接触到的哲学和科学范畴内,能够被证明的宗教真理。因此,克劳利对西方神秘学的独特贡献在于,他通过诉诸形而上学和经验主义怀疑论,去合理化他自身的进路,尽管这些进路本质上是宗教式的。他的首位批判性研究者Fuller将克劳利的形而上学立场描述为一种“克劳利主义”(Crowleyanity):这一术语的意思就是读者愿意咋称呼就咋称呼,你说他是什么“怀疑论+琐罗亚斯德思想”、“怀疑论+神秘主义”、“怀疑论+超验主义”、“怀疑论+通神术”、“怀疑论+能量理论”、“科学化的光照论”等等,都行。但反正就是,简而言之,他就是以无神论者的姿态有意识地去连通上主——即:以怀疑论的工具去超越理性,又以对绝对者的直接意识去限制怀疑论。克劳利认为,当代的科学和启示性宗教囿于固有方法论的局限,都无力回应自身的问题,要想认识终极真理,则必须结合二者在认识论上的优势。因此,克劳利给自己的神秘学刊物《春分》杂志选择了这样的刊铭:“以科学之方法,达宗教之目的”。魔法便是这第三条路径。
克劳利是一个相当复杂和多面的人物,他一生的活动范畴涵盖了登山、诗歌、比较宗教、政治、小说、象棋、神秘主义、以及关于泰勒玛(Thelema)和魔法的艺术。读者应该重点关注最后两样事物。

1912年的克劳利
3.世代论
克劳利鲜明的个性,与其个人理论和实践发展紧密相连。虽然如今关于克劳利有几本传记,但是这些传记中蕴含的丰富细节,往往遮盖了他智性和灵性生涯的主线和发展趋势。
克劳利生于1875年,其家族乃是一个标准的维多利亚时代中上层家庭。克劳利的家族有别于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化,因为他们全面沉浸于普利茅斯兄弟会的闭关兄弟会(Exclusive Brethren,EB)派别的宗教文化,这一派是一种福音派的基督教复兴运动。因此,兄弟会高要求的宗教实践、僵化的道德规范(以及明显的虚伪),滋生了克劳利青春时期的叛逆情绪。在克劳利叛逆的阶段,他通过将自己置于与家族所敬奉的上主明显对立的位置,而达到一种与家庭的切割。他所找到的这个“对立面”的模范便是《启示录》中的“大兽”(Great Beast),而《启示录》正是普利茅斯兄弟会用历史-语法学阐释圣经的主要文本。约翰·达秘(John Nelson Darby)(注:此人虽然跟神秘学本身无关,但是在现代新宗教历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是这一运动的核心人物,他提出了一套基于前千禧年主义的世代论神学(premillennial dispensational theology),极大地塑造了克劳利本人的世界观。
世代论(【法国专题01】玄秘宗师列维-人物小传)会将圣经历史解释为一系列的“世代”,这些世代以上主和其子民的盟约为标志。前千禧年主义指向了一个至福的未来世代,在这一世代里,伴随着基督的回归,上主的统治将在凡间得以全面实现。对克劳利而言,毫无疑问,他出生的那个世代注定要被一个即将来临的弥赛亚给掀翻。
克劳利后来就读于剑桥大学,但是没有获得学位,他在获得了启示之后,便将自己的人生奉献给了宗教事业。从一开始,他所献身的事业就以两种形式呈现——性和神秘学。对于前者而言,不需要到学校学习也行。而关于后者,他在1898年发现了黄金黎明协会(【黄金黎明专题01】秘会的开端),对他来说,黄金黎明似乎可以提供关于西方神秘学的权威教导,也可以提供启蒙入会之门户,以通向那隐秘的玫瑰十字教团。但是克劳利并没有在黄金黎明协会停留太长时间,那时,协会因为其历史合法性问题、以及关于创始人之一的马瑟斯(【黄金黎明专题02】马瑟斯:典仪的奠基者)的权力问题产生了巨大的争执,最后伦敦本部因为这些纷争而分崩离析。黄金黎明体系以卡巴拉生命之树为基底,综合了西方神秘学的各项知识,且以此为结构,建立了等级制的启蒙晋升秘会结构。这种组织结果仍然对后世的神秘学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对克劳利而言,黄金黎明协会并不是那个“隐秘的圣杯教会”(Hidden Church of the Holy Grail)的化身,因此,他便转向东方,寻求印度、缅甸的佛教和瑜伽的智慧。在黄金黎明的系统中,东方神秘主义并不占据一席之地。但克劳利发现,通过瑜伽训练可以提升专注力,这可以成为西方神秘学的仪式中一个有用的助益。

《启示录》中的“大兽”
4.天启与传道
对克劳利的人生来说,有一项绝对性的改变发生于1904年四月的开罗。那一天,克劳利和他的妻子正在实践一项仪式魔法的召唤术,但突然,(正如克劳利对这个故事的叙述)他的妻子说,埃及的荷鲁斯神正在等待着他。按照她的仪式指令,随后,克劳利声称自己经由直接启示,获得了一本文献——此即《律法之书》(The Book of the Law)。本书启示了一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而以“大兽”身份出现克劳利,就是这个新时代的先知。过去的世代被称为“奥西里斯纪元”,其表现为父权制的宗教和社会结果,而即将到来的则是“荷鲁斯纪元”,他是神子,象征着个体的绝对自由。希腊语“泰勒玛”(Thelema)在英语里就是“意志”(Will)的意思,这个词语在“荷鲁斯纪元”里面,将会是代表“律法”的“词”。概括了一句看似非常反传统的箴言:“为汝所欲为”(Do what thou wilt)。(注:整句话为“Do what thou wilt shall be the whole of the Law”,译为“为汝所欲为,即为汝之法”,或“作你要作的乃是律法的总纲”)
克劳利并没有很快接受《律法之书》赋予他的领袖权威。但是,他认为这个启示是让他占据马瑟斯所留下来的灵性领导者的位置。于是,在1909年,克劳利创建了“银星十字会”(A∴A∴),他融合了黄金黎明的西方神秘学实践和他所学习的东方神秘主义实践,并构建了一个基于师徒传承的权威等级体系。在半年刊物《春分》(The Equinox,1909-13)中,他发布了自己教团的知识内容。马瑟斯则起诉克劳利在《春分》上“剽窃”(【黄金黎明专题01】秘会的开端)了黄金黎明内层教团的仪式。而这些发表的内容直接促使克劳利成为另一个“新玫瑰十字会组织”——东方圣殿会(the Ordo Templi Orientis,OTO)的领导者。东方圣殿会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共济会团体,以一种严格守护的秘传内容——性魔法的理论与实践——为核心。在1913年底,克劳利启程前往美国,其间,以上两个相互关联的神秘学运动(注:即银星十字会和东方圣殿会)在他的引导下不断发展,成为他宣传“泰勒玛启示”和“荷鲁斯纪元”的工具。类似于黄金黎明协会,两个神秘学团体都拥有一小撮成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克劳利一直呆在美国,此后,他所领导的小团体和追随者广泛活动于加拿大、英国、南非和澳大利亚。遗憾的是,克劳利领导的运动并没有铺展开来,他的书在市场上鲜有人问津,大部分时候他都是默默无闻地往来于欧洲与北非之间。直到他的小说《瘾君子日记》(1922)问世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才短暂地打破了他人生的沉寂。1920年,克劳利在意大利西西里的切法卢建立了一个乌托邦社区,名为泰勒玛修道院。对克劳利及其追溯者而言,这个社区乃是一个“学院兼灵性圣所”(Collegium ad Spiritum Sanctum),其直接指向圣灵(Holy Spirit),学员们可以在这里修习银星十字会的各种知识,例如瑜伽实践或是魔法仪式。1923年,墨索里尼将克劳利逐出意大利,随着克劳利的离去,这个社区也就逐渐消亡了。他所写作的教材《魔法的理论与实践》(1930)几乎没有得到传播。他的其它神秘学文献都是私自印刷出版的,出版数量极其有限,主要是提供给他的门徒和学院使用。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是《托特/透特之书》(The Book of Thoth,1944),这本书是他对塔罗奥义的阐释,在他的指导下,“透特塔罗”也伴随这本书被设计出来。
1947年,克劳利在英格兰的黑斯廷斯去世,美国的《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这样的杂志将他塑造为“行游在社会边缘的宗教怪咖”。几十年来,这种观点一直是人们对克劳利的主流认知。

美国女演员简·沃尔夫在泰勒玛修道院附近的海滩边冥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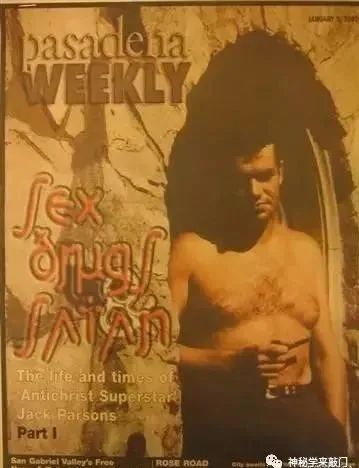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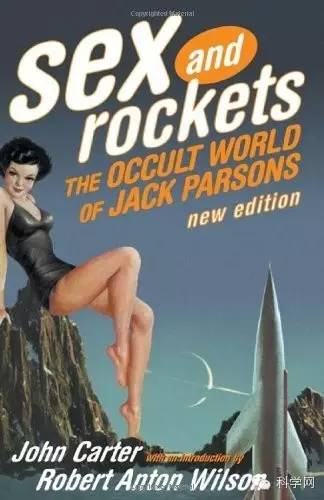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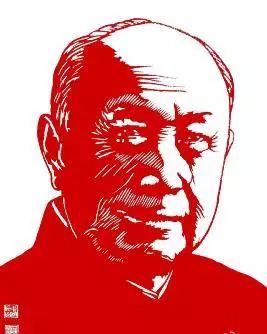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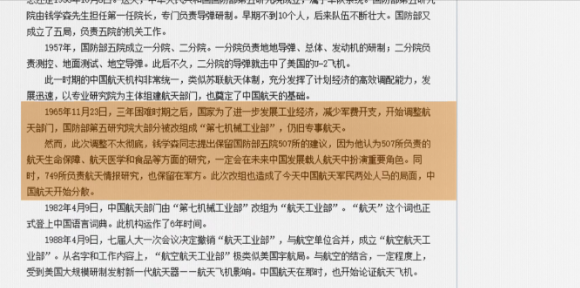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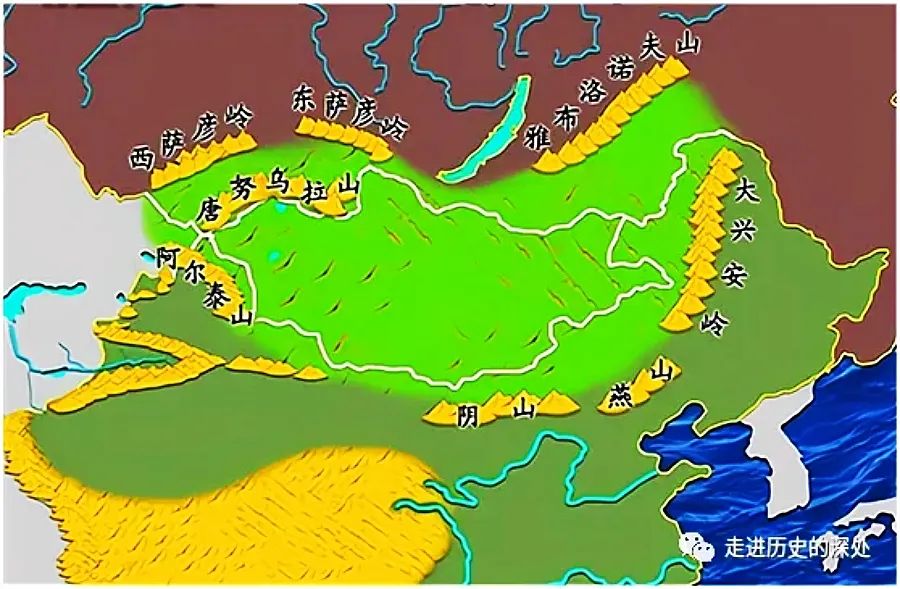











我来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