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的尽头是摇滚,摇滚的尽头是宗教



铺天盖地,今天一下子我微信视频推送都集中在赵雷最近演唱会的几首歌上:《我们的时光》、《阿卜杜拉》。这都踩在我的音乐频谱上。我并不太喜欢更被大众传唱的《成都》。赵雷的乐队现在非常懂得营造气氛,他们的美女郜一菲的小号、祝子的笛子逐渐演变成灵魂,我也认同这两人确实给乐队带来新的感觉,音乐层次感和冲击力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但不管如何,赵雷的歌在我看来,始终是他写的歌词非常有感召力,非常有画面感,几乎每首都是一首不错的现代诗。始终,我喜欢歌曲的文学性,要优于旋律的美感。所以,就算郜一菲吹《南方姑娘》时扎得长辫非常让人陶醉,她的慵懒微胖身姿是所有男歌迷欣赏赵雷乐队最美的风景线,但依然不能改变整个赵雷乐队那种特定的风格。
我个人很喜欢民谣。而且一般比较小众,从最早期的校园民谣潮到后来的独立单品,如叶蓓、水木年化、许巍、朴树、李健到后来的李志、宋冬野、赵照、万晓利、周云蓬。赵雷也是。当年《中国好歌曲》赵雷一首《画》真让人惊艳。他如果好好写歌词,水平不在许巍和宋冬野之下。许巍的《两天》入选《中国当代诗歌文选》的,宋冬野的《郭源潮》意境深远,而赵雷写实,不经意间就会让听他歌的人泪流满面,因为简单、会直击心灵。不记得是谁说的,好的歌,就是当你听过之后,若干年再去听,哪怕只是那么几个小节,或者一句熟悉的歌词,仿佛一下就回到最初听到它的那一刻,不由自主再次泪流再次被感动。很神奇。
都说“民谣的尽头,便是摇滚”。我怎么感觉摇滚的尽头才是民谣啊。很多年以后才明白,摇滚是民谣的尽头说的大概是在欧美海外音乐圈,国内大概流行另外一个规律:人年轻时躁动,所以反叛,喜欢挑战一切;而且玩摇滚很cool,摇滚的精神是不屈,是自由理性和不妥协,这是一种成长。就像鲍勃·迪伦的那首《Like a Rolling Stone》是他从民谣歌手走向摇滚旗手标志一样,电音和重金属旋律改变了民谣叙事体风格,似乎是一种反叛但又不全是,所以跟中国文化的成熟随着岁数增长渐进的逻辑相反。我觉得这个反差挺有意思。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不会再有,现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似乎也不太有合适土壤去生长所谓嬉皮士这类人群,上世纪60年代的青年似乎都迷茫,一如现在,但性质已然不同。60年代初中国的年轻一代积极在革命造反、在上山下乡,比美国年轻人要反叛激进得多;美国二战后婴儿潮一贯精神弱,反而非常羡慕革命,比如古巴的切·格瓦拉。他们整天喊着反战、爱情、和平,但这些人又不是真正意义上地会主动积极参加到社会实践的,而是回避,想着如何追求梦幻世界,迷幻自己。虽然懂礼貌、守法、有文明,但就是一个彻底的消极阶层,大概跟现如今“躺平族”差不多。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创造了摇滚精神,又亲手熄灭了它,最后那次混乱的美国小镇数十万来自世界各地青年一起制造了最有名的骚乱,很多议题都成为后来的禁忌。
所以美国人的摇滚后来也不“积极”、“进步”,甚至变得越来越堕落,但摇滚的“精神”则成为某种都实现不了的“虚幻”,被人供奉在祭祀它的神龛里,藏在全世界年轻人挥动的手势里。而且老的摇滚客已经不再年轻,现在的年轻人似乎一下就成熟了,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喜欢进入政府工作,都喜欢当文职,变得不那么激动,追求心灵安逸。
所以,民谣半生不熟,摇滚熟透了,就成为宗教,成为某种信仰,让人爱信不信。
乔布斯当年也是愤青,也喜欢摇滚,后来皈依了神秘的东方佛经禅宗。许巍摇滚青年到最后抑郁,一度痛不欲生,后来也“穿透了幽暗的岁月”信奉了佛教。那位吹笛子的大神窦唯,后来创作的音乐作品就有点古谱古曲,放到寺庙里做背景更好。所以国内摇滚圈子里流传一句话:张楚死了,何勇疯了,窦唯成仙儿了。
据说西方最知名的宗教音乐祖师爷是钢琴家巴赫,他的复调对位法创造方式,宗教性很高,旋律拍子异常贴近人的身体频率,非常舒缓,多燥热的人只要听听巴赫的安魂曲就能迅速安静下来,现在在日本有人甚至给奶牛听巴赫来促使多产奶。
我相信,赵雷乐队这波吹小号的美女参与,是从他的民谣风格向摇滚过渡的一个小浪花,最后的小倔强,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肯定也不会免俗地往宗教上靠,很可能就是中国特色的佛教,而且特指是一般大众都喜闻乐见的“净土宗”,暮鼓笛子古筝更多些,这几乎是可见的必然。
我先去敲敲木鱼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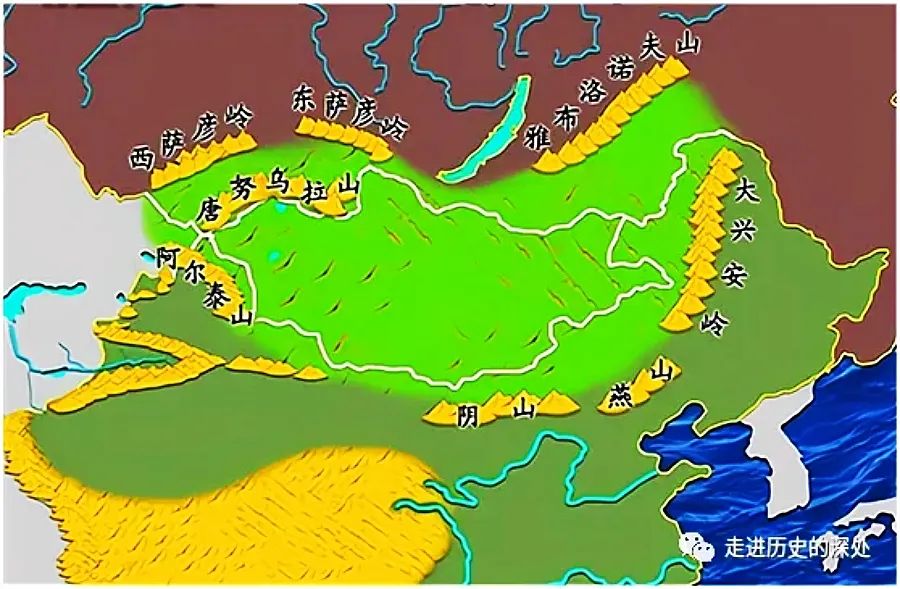











我来说两句